刘元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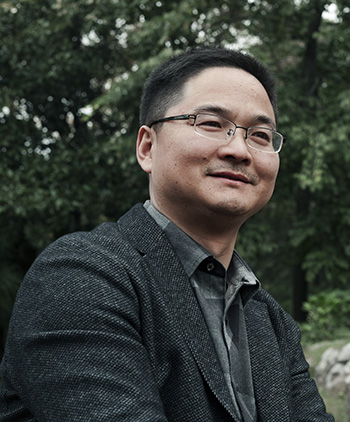
刘元堂
1人物简介
刘元堂[1-3],男,1972年生,山东乳山人。南京艺术学院书法博士。山东大学古文献博士后。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书法作品曾参加首届中国书坛兰亭四十二人展、首届全国青年展(获最高奖)及八届国展(获奖提名)等展览。2010年在山东省美术馆举办个人书法展,并出版《刘元堂书法集》。现为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书法系教师。
2参展获奖
书法作品:
2000 全国第八届中青年书展 入选
2003 全国第二届行草书大展 二等奖
第二届流行书风展 入展
2004 首届全国青年书法篆刻展 获(最高)奖
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展 二等奖
全国第八届书法篆刻展 获奖提名
2005 山东省第六届青年书法展 一等奖
2006 2006中国书坛青年百强榜 书法十佳(并列第一名)
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 入展
纪念建党85周年书法展 三等奖
2007 首届中国书坛兰亭四十二人展 入展
全国第九届书法篆刻展 入展
2011 第二届中国书坛兰亭四十二人展 入展
3书法文章
博士论文《宋代版刻书法研究》 获江苏省研究生创新工程
硕士论文《中皇山北齐佛教刻经书法研究》被评为江苏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书法创作姿势论》 《艺术百家》2011年第6期
《方石书话》书学思想抉要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趋古避俗难自立----米芾不胜草书原因试析》 《中国书画》2007年第6期
《 在水一方》 《书法》杂志2007年第2期
《小字情缘》 《书法报》2007年8月29 日第34期
《米芾与大草》 《书法报》2006年4月26日
《欲问此中妙,自言我先知——魏启后先生的学书自述》
《书法导报》2006年5月24日
《吾爱吾师》 《墨痕》2005年第2期
《秀才吴怀民》 《广西画报》2008年第4期
4息斋散文
在水一方
刘元堂
莫非先祖是依据它的形状而创造了“泉”字?它,静静地镶嵌在村南山坳的石硼间,清清亮亮的一泓,像荒山野岭的眼睛。身下时断时续的溪流,仿佛眼睛淌出的泪水。
村子里代代相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很久很久前的一年,天下大旱,江河干涸,草木枯竭。一群干渴的人在方圆几百里的山野间跋涉了好多天,竟没寻到一滴水。这是一个死寂的黄色世界,黄日头,黄山崖,黄天黄地间弥漫着黄沙。年迈的老族长陡觉眼前一暗,一头栽倒在黄土上……再度醒来时,他的耳边隐约传来一串叮叮咚咚的音符,他狂喜地睁开眼,迎接他的却依然是苍黄的世界。原来是幻觉!但当他重新阖上眼睛时,那玲珑清脆的声音又轻轻传来了。老族长跌跌撞撞一路寻去,身后紧随着满怀希望的褴褛人群。在一声嘶哑的长叫后,他轰然倒地。这一次他的眼睛再也没能睁开,枯柴般的手却指向了这眼灵泉。逃亡的人们知道这里就是新的安身立命之所了。于是便有了我们那个小小的村庄。
或许基于祖上对泉水的崇拜,我自幼对水便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感。而那眼泉和它身下的小溪,给我儿时带来无比的快乐。夏天可游泳其中,冬天结冰后则嬉戏其上。即便是溪里的小鱼小虾,自由自在精灵一样生活着,也让我羡慕不已。
李白曾有“古来万事贵天生”的感叹,我相信任何人生来都带有异乎寻常的灵性,只是或多或少而已。七岁学识字时我发现另一件令我愉悦的事情:村东头那幢房子山墙上用毛笔写着“山东省乳山县诸往公社扫帚涧大队”一行大字,笔力遒劲,结体端庄,我隐约能感觉到隐藏其中的美了,禁不住用木棍在地上比划起来。上小学一年级,我的铅笔字便成了班上同学争相效仿的范本。三年级学写大仿,老师以示表扬的几个红圈圈,更加深了我对写字的喜爱。自此,书法与我正如溪水与泉,相依相伴,生生不息。
济南,“济水”之南,一个处处与水有关的地方。黄河雄卧其侧,七十二名泉错落其间,赵孟頫那幅《鹊华秋色图》中的一叶扁舟,承载着我对水乡般的济南无尽向往。只可惜在我来到济南时,“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景色已不复存在,黄河断流,泉水停涌。但这并不影响我学习书法的热情。当我被一位长胡子老人的楷书笔法折服后,那天夜里我虔诚地坐在他的面前,听他诉说昔日济南泉水之清澈,鱼虾之丰富,以及黄河鲤鱼之美味。不知是何话题引起了老人对其书艺高超却穷困一生的恩师的回忆:“先生八十多岁还靠捉蛐蛐卖钱养活自己。我把他请到家里来,给他煮两个鸡蛋,他只能吃一个…… ”泪水模糊了老人的双眼,语音竟哽噎起来。那夜出奇的静,风儿,蝉儿,工厂的机器都屏住了呼吸。老人的哽噎声震耳欲聋。我决意拜老人为师。
那位老人便是张弩先生。张先生用一支长锋羊毫演绎着从其老师处继承的碑派笔法,并总结出一套科学的楷书结体方法。他重视法度,主张“法不厌精,法不厌细,法不厌多”。我从先生处受益最深的是“笔笔断,笔笔连”法,该法要求笔锋不停地在纸面上跳动的同时讲究气韵的连贯和节奏的起伏,像武林高人手中的梅花枪,神出鬼没,变化万千。米海岳一个“刷”字,后人猜测了近千年。我用“笔笔断,笔笔连”法去临米书,竟是那样的得心应手,了无挂碍。
天下之水,莫大于海。我在威海一栋可以看见大海的楼房中安家时,已年近而立。威海是一座新兴的海滨小城,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它没有古城的城池楼阁和小桥流水,同时也就没有了园林般的刻意与小气,有的是波涛滚滚的大千气象;它没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同时也就没有了泥沙俱下的文化垃圾,有的是海风般的清新和纯洁;它没有德高望重﹑技压群芳的书坛老宿,同时也就没有了笼阴遮阳的大树,有的是可让幼苗茁壮成长的阳光和雨露…… 在威海的日子,我时常一人独坐海边,观云卷云舒,听潮起潮落。我想书法的精神,应该像海浪一样,自由奔涌在无际的沧海里。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面状的西湖,线状的钱塘江,点状的村舍,杭州一定是上帝最得意的一幅山水画。二零零四年正月,我同来自天南海北的二十几位同学相聚杭州,求学于那所著名的美术学院。我们租居在钱塘江畔的一个叫珊瑚沙的村子里,村头连片的水塘,村里蜿蜒的小巷,家家院子里的芭蕉,一切都充满了诗情画意。生于北方长于北方的我,仿佛住进余光中的诗里了。每日清晨,我会爬到村子对面的山坡上读英语。晨雾如带,似乎伸手就可摘它下来。树间打闹的松鼠,时常打断我的读书声。读累了,采一片嫩绿的龙井茶,未及送进嘴里,已是满口清香…… 往昔怀素“观夏云随风变化,顿有所悟,遂至妙绝”,黄庭坚“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杭州的湖光山色同样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那年春天我佳作连连,一如江水绵绵。
书法史总是太狭隘。“ 一笔书 ” 怎能是张芝所创?九州大地为纸,长江便是书于其上的“一笔书”。张芝能有如此大的气魄吗?偌大的“一笔书”写到南京时,作收笔前的轻轻一顿,便自自然然地流入了大海。就是这轻轻的一顿,长江文化所有的积淀,都汇聚于南京城了。无怪南京的书家自古才气充沛,底气十足。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感叹道:不到南艺,不知什么是美女如云!不见徐师作大草,不知什么是痛快淋漓!的确,我无法拒绝南艺对自己的诱惑。南艺校园蝴蝶般飘舞的美女,大概个个都是金陵十二钗的后人,袅袅婷婷,目光如水。而徐利明先生的大草一定是借助了长江的气势,浩浩荡荡,气贯长虹。
徐先生的“连绵法”迥异于张先生的“笔笔断,笔笔连”法。前者笔不离纸,连绵不绝。后者笔纸常离,跌宕起伏。如果说徐先生演奏着江南丝竹,弦声悠悠,那么张先生则是敲打着山东大鼓,鼓声咚咚。张先生用十年心血把我培养成一名较为优秀的鼓手,而当我向徐先生请教他弦乐般的笔法时,他却说:“去写写篆隶吧,去赋诗作画治印吧,去听听钱塘江潮吧……”。我知道,他要我用一生的时间去成就自己。
两年后我将完成在南京的学业,或许我会去另一个洋溢着水的美妙传说的地方……
我的书法,在水一方。
2006年8月于威海
在路上
刘元堂
2010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初八。
上午八点四十五分,我匆匆登上威海发往南京的卧铺大巴。我的铺位在最后一排,身下便是轰鸣的发动机。铺位狭小,床面沾染了多处污秽。窗外,站着我的母亲、爱人,还有我八岁的女儿。柔弱的妻子,眼角早已湿润。我朝她装装鬼脸,她也跟着苦笑。我母亲,这位给予我莫大支持的伟大女性,眼角刚要流泪,便强忍回去。她把注意力转移到那辆老旧大巴的行李箱上,她担心行李箱门会关不严实,而使我的几个旅行包失落在途中。女儿却一反常态,朝我扭扭屁股,摆摆手,做几个我俩合编的pose,快快乐乐的样子。我大声喊着让她们回去,让爱人路上开车多加小心,她们也朝我喊些什么,而隔着厚厚玻璃,我们彼此听不见。听见的,只是将要远行的大巴发动机轰鸣声。
九点,大巴准时出发。在拐弯处,我回过头,看到女儿拖着她奶奶已离开,妻子却仍旧站在那里,目送着即要离开视野的大巴。
行至文登,上来一位带着三岁女孩的夫妇。女孩哭泣着用一口地道的文登话问:“奶奶呢?奶奶为什么不上来?”。“我要奶奶!我要奶奶!!”她爸爸告诉她:“奶奶在下一班车上!”女孩不信,依然哭泣,且哭声愈来愈悲切,甚至有些撕心裂肺。男子告诉我,他和妻子在南京工作,女孩一直在老家由奶奶带着。人生自古伤离别,何况是骨肉分离,又是在这大年期间呢?我心头一酸,自口袋里摸出纸巾……
下午两点,打电话给妻子。妻子告知,母亲已回乳山老家。女儿接过我的电话,问我下次何时回家。我说两个月爸爸就把手头的论文写完了,就可以回家了。不料女儿突然哭了起来,喊着要都都(女儿对我的称呼)。一个多小时后,妻子打过电话来,说女儿躲在书房,一直哭到现在。哭泣的过程中用毛笔画了一个都都,圆圆的脸带,方方的眼镜,十分传神。并且题款曰“都都早回家!”,字写的很端正。
在狭小的铺位上,辗转反侧,看了一会书。眼睛发涩,便移向窗外。这条路线的风景,我并不陌生,来来往往已经走了近五年。但我第一次发现这样一种景象:路经的每一个村落,其旁总有一个坟地。从山东到江苏,村落的房舍有些区别,坟墓的修建也不尽相同,但二者之间总近在咫尺。人们在村落里出生、成长,其归宿无不是坟地。无论如何声名显赫,无论如何默默无闻,他们都是行走在村落通往坟地那段短暂的路上。可以说,人生的轨迹便是从村落走向坟地。
从村落到坟地,人生的路,如此短暂。想想自己假期在家,充斥着不快。这又何必呢?
下午三点,车停在赣榆境内吃饭。一位乘客说自己的钱包丢了。后来在卫生间的小便池里找到。几百元钱没了,但身份证等证件还在。小偷也越来越讲究职业道德了。
路上不断上客,车里人满为患。一个体重二百多斤的小伙子,看不下过道里侧坐的带着四个月婴儿的母亲,把自己的铺位让出来。到前边和一个中年体胖医生挤在一起。医生不满,说你年纪轻轻就胖成这样。小伙回答说,我胖是有原因的。我为一个患白血病的小男孩捐献了骨髓,以后就越来越胖了。医生说,你老了会更难受。小伙说,我早就知道,我母亲就是一位军医,她不让我去捐献。但我看不下那孩子可怜巴巴的眼神,还有他爷爷彻夜跪在我家门口那种神态……我问了一句,那孩子康复了么?小伙子笑着答到:都七年了,很健康! 每年都打电话给我拜年!
晚上九点半,汽车进入南京市区,我在江北站下车。实在不愿回学校的宿舍,那间背阳的屋子,几天不住便会发酵出刺鼻的霉味。在江北,我和同级的国画博士刘懿合租了一栋百余平方的工作室。三十楼,面向长江。把酒临江,总会有无尽的灵感。我们名之曰“揽江楼”。打开揽江楼的门,一股冷气扑面而来。毕竟一个多月没人住了。摸摸被子,照样潮湿。刘懿尚需几天返回。在这所不属于自己的城市中,在这冷寂的屋子里,孤独感油然而生。想起徐勤海,这位与我一起硕士毕业直到年前才找到工作的好友,租住在离揽江楼不远处的村落里。发短信问他在哪里,回道在山西运城。该来的人没来,该走的人走了,该孤寂的人在孤寂。在潮湿的被窝里,我努力使自己入睡,但路上所见所闻萦绕在脑际间,我陷入不得答案的思考:
我在求学路上。母亲及妻女在盼望早日团聚的路上。小女孩在离开奶奶到南京接受教育的路上。小偷在苟且偷生的路上。捐骨髓的小伙子在助人为乐的路上。徐勤海在刚参加工作的路上……
人们都行走在路上,行走在村落通往坟地的路上。这段路很短,人们的行走却是很匆忙。越是匆忙,离终点越近。
如果站在路上,原地不动。那样岂不是可以延长生命?
如果回过头来往后走,就永远不会老了。
我很得意,似乎找到长寿秘诀。
可如何原地不动呢?又如何往后走呢?
显然行不通!
那就走慢一点,延长到达终点的时间。
这个似乎好办!让自己的生活节奏慢一些即可。
……
已是下半夜。我告诫自己:抓紧睡吧,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们永远行走在路上,匆匆忙忙!
2010年2月23日于南艺研究生宿舍11号楼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