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过云楼之一】 顾笃璜回忆录(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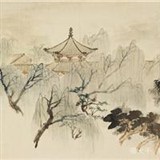 江苏凤凰拍卖国际有限公司·2013-07-15 0条评论
江苏凤凰拍卖国际有限公司·2013-07-15 0条评论 
怡园曾组织中国画与西洋画比赛
当年的过云楼名噪江南乃至全国,想到过云楼看画的人也越来越多。过云楼第五世传人顾笃璜先生回忆说:“当时来看画的人无非是两种人,一种是真能欣赏的,一种是需要培养的。”顾老的助手还补充介绍:“顾老家有看画的‘十三忌’,规矩颇为详细,其中有对天气等的要求,也有对人品的要求。顾家对看画人的为人看得很重。”外人仰慕顾家宝物多多,富甲天下。而对顾家人来说,保护、保存好这些藏品是“责任”,寻找到它们好的归宿也是心事。顾老说:“像过云楼最后1/4的藏书收归凤凰(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我还是满意的。”
父子通信谈过云楼收藏
“我高祖(顾文彬)写信给儿子(顾承)交代各种注意事项,而儿子在家里如何操办过云楼,也都写信向父亲汇报,这些信件都很详细记载了过云楼的收藏过程,包括怡园的建造。我高祖写给儿子的信可以装订成六册,都是手稿。它们本身不是信,而是信稿,当时要先写好了稿子,再写在信上。这些信件研究起来挺有趣的。”
“过云楼的藏品在外人看来是宝贵的财富,但是对顾家来说是种负担,也是责任。”
“抗战的时候,苏州有个人跟顾家有过关系,他在戏院里做投资邀角儿的活,企业家高价来买票,然后他再拿来送人。后来他发财了,儿子在日本留学,在上海虹口开工厂。因为他家卡车司机是日本人,通过这层关系(有日本司机打掩护),我们的东西运到上海都是通过他的车子。”
“那时候,我伯父(顾公雄)的藏画都在常熟,因为常熟是他丈人的家,后来也运往上海,因为车上装满了书画古籍,无法坐人了,无奈之下,伯父就决定把两个儿子留在常熟汽车站一家小店的阁楼上,先将文物运往上海。上海的亲戚见了面就问:‘孩子呢?’他这才急起来:‘喔唷,还在汽车站!’从此顾家亲友常笑话他只要书画,连儿子都不要了!”
怡园的建造与画赛会
“我们家的怡园是由画家任熏(任阜长,四任之一,海上画派代表画家)等人参与设计。任阜长懂建筑。外面人说是任伯年设计的,其实不是,任伯年当初是被人介绍到苏州给任阜长做徒弟的。后来任伯年和吴昌硕到上海,和吴昌硕搭档,成为海派画家。任伯年没文化,字写得不好,大部分作品都是任伯年画画,吴昌硕题字。”
“怡园有个著名的景点叫‘石听琴室’,有五块太湖石竖在那里,石头怎么能听琴呢?其实说的就是一种意境。因为‘太平天国’之后,很多园林破败了,不少太湖石流散出来。我们家就此买进了许多太湖石,看到这样五块形态各异的石头想用它们布个局,就造了个房子。我们家人都会弹古琴,家里有东坡琴(苏东坡用过的古琴),因此怡园里关于古琴的有两处房子,一个叫石听琴室,一个叫坡仙琴馆。以前,过云楼门前也有五块石头,‘大跃进’时被用去炼石灰了。”
“怡园画社是苏州第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书画社团,这证明我祖父顾鹤逸的思想还是比较新的。而且他不排斥西洋画,曾经建立了一个由西洋画家和中国画家联合起来的组织,他是社长。这个组织起初叫画赛会,每年举行一次比赛,后来又成立苏州美术会。他自己出资建造会所,就在我们老宅的对面,还出版刊物——《美术》半月刊,可惜现在一本也找不到了。”
藏品是责任不是财产
“其实,过云楼堪称精品的藏书,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我祖父顾鹤逸买来的,当时苏州的一个收藏家去世,他的儿子把书拿出来卖,我祖父恰巧全部买下来。在我看来,这批藏书的最大价值并非《锦绣万花谷》,而是上面有黄丕烈的批注,这才是最有价值的。”
“的确,很多博物馆都接受了我们家的藏品捐赠。当时捐赠这些东西,有很多人认为,肯定是迫于一定的压力。我声明,一点都没有,完全是自觉的,因为在我们家人看来,这不是我们家的财产,而是我们的责任。经过战乱保存下来不容易,当时只觉得捐给国家,得到保护了才是最好的归宿,脑袋里没有出现过钱的问题。比如那四分之三的藏书捐给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还给了几千块钱奖金,我们家又将这些钱捐给‘抗美援朝’了。为保护这些藏品,我们家租了个保险库存放书画,每年都要付钱。”
“在我看来,这些藏书藏画的价值不是在于它后面有几个零,值多少钱,而是文化价值,这是无价的。藏主很重要,像过云楼的四分之一藏书收归凤凰,我还是满意的。”
